目录
快速导航-
中篇小说 | 穿胸族少女
中篇小说 | 穿胸族少女
-
短篇小说 | 下了一星期的雨
短篇小说 | 下了一星期的雨
-
短篇小说 | 外星人
短篇小说 | 外星人
-
短篇小说 | 一包汤
短篇小说 | 一包汤
-
短篇小说 | 别途
短篇小说 | 别途
-
短篇小说 | 香椿的事
短篇小说 | 香椿的事
-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沂蒙之花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沂蒙之花
-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蒙山恋歌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蒙山恋歌
-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那些身影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那些身影
-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少年的抗日战场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少年的抗日战场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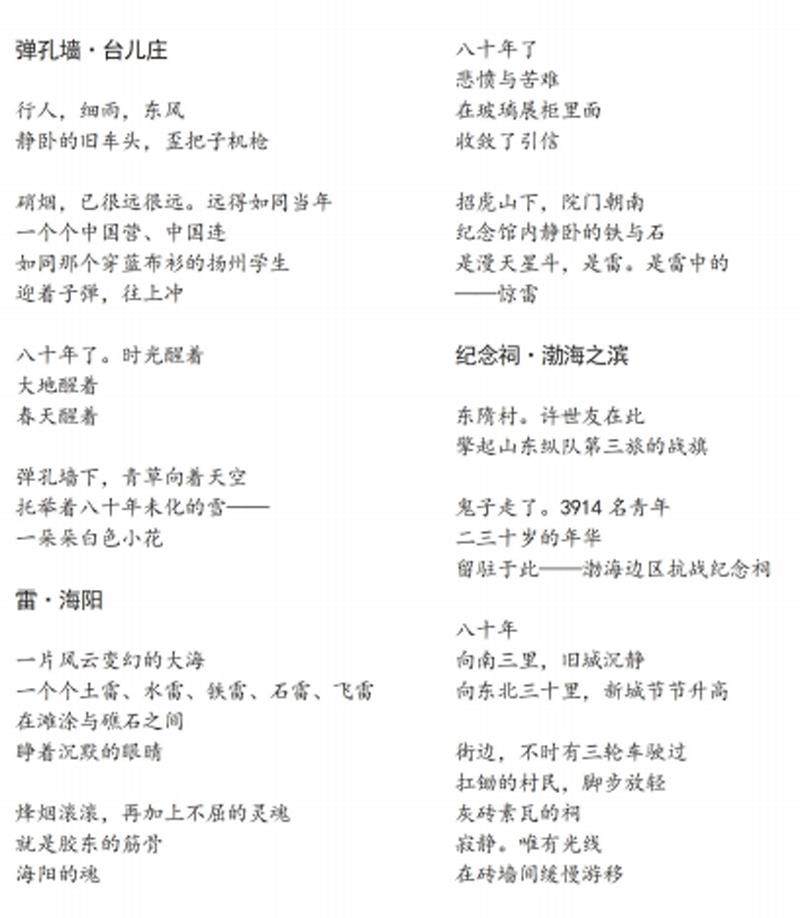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弹孔墙 (组诗)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弹孔墙 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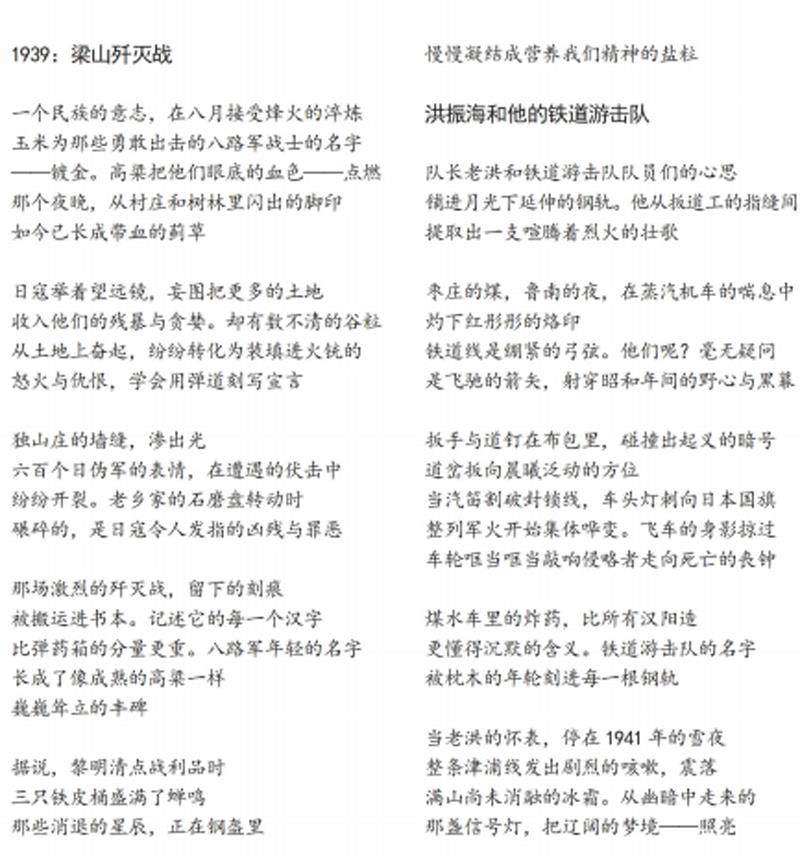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硬骨与精神 (组诗)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| 硬骨与精神 (组诗)
-
散文 | 金鸡独立图
散文 | 金鸡独立图
-
散文 | 最初的词语
散文 | 最初的词语
-
散文 | 银杏树叶
散文 | 银杏树叶
-
随笔 | 古道与古场
随笔 | 古道与古场
-
随笔 | 巴岱与黑头羊
随笔 | 巴岱与黑头羊
-
随笔 | 随笔三題
随笔 | 随笔三題
-
诗歌 | 野漆树 (组诗)
诗歌 | 野漆树 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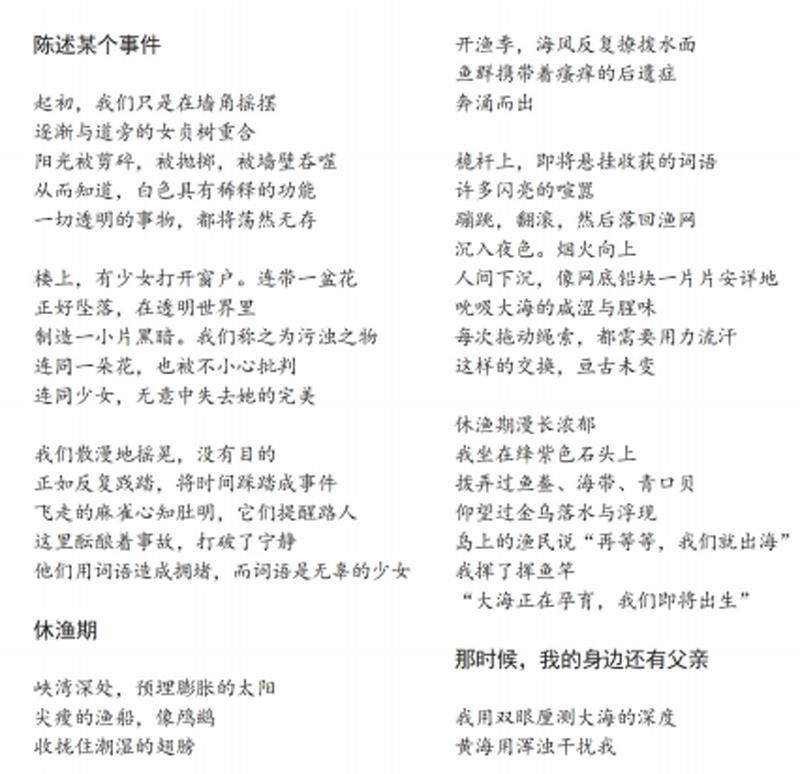
诗歌 | 大海正在孕育 (组诗)
诗歌 | 大海正在孕育 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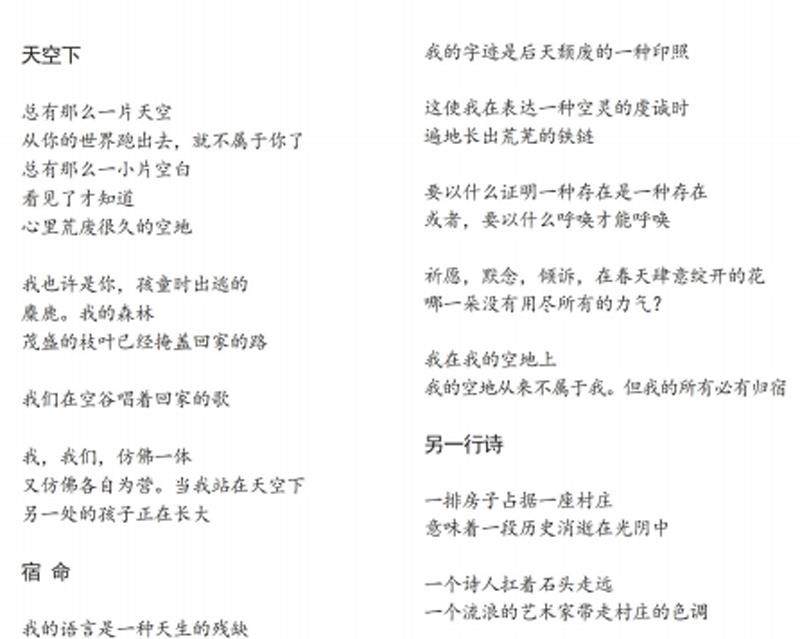
诗歌 | 捧起一抹沉雪 (组诗)
诗歌 | 捧起一抹沉雪 (组诗)
-
诗歌 | 永生(组诗)
诗歌 | 永生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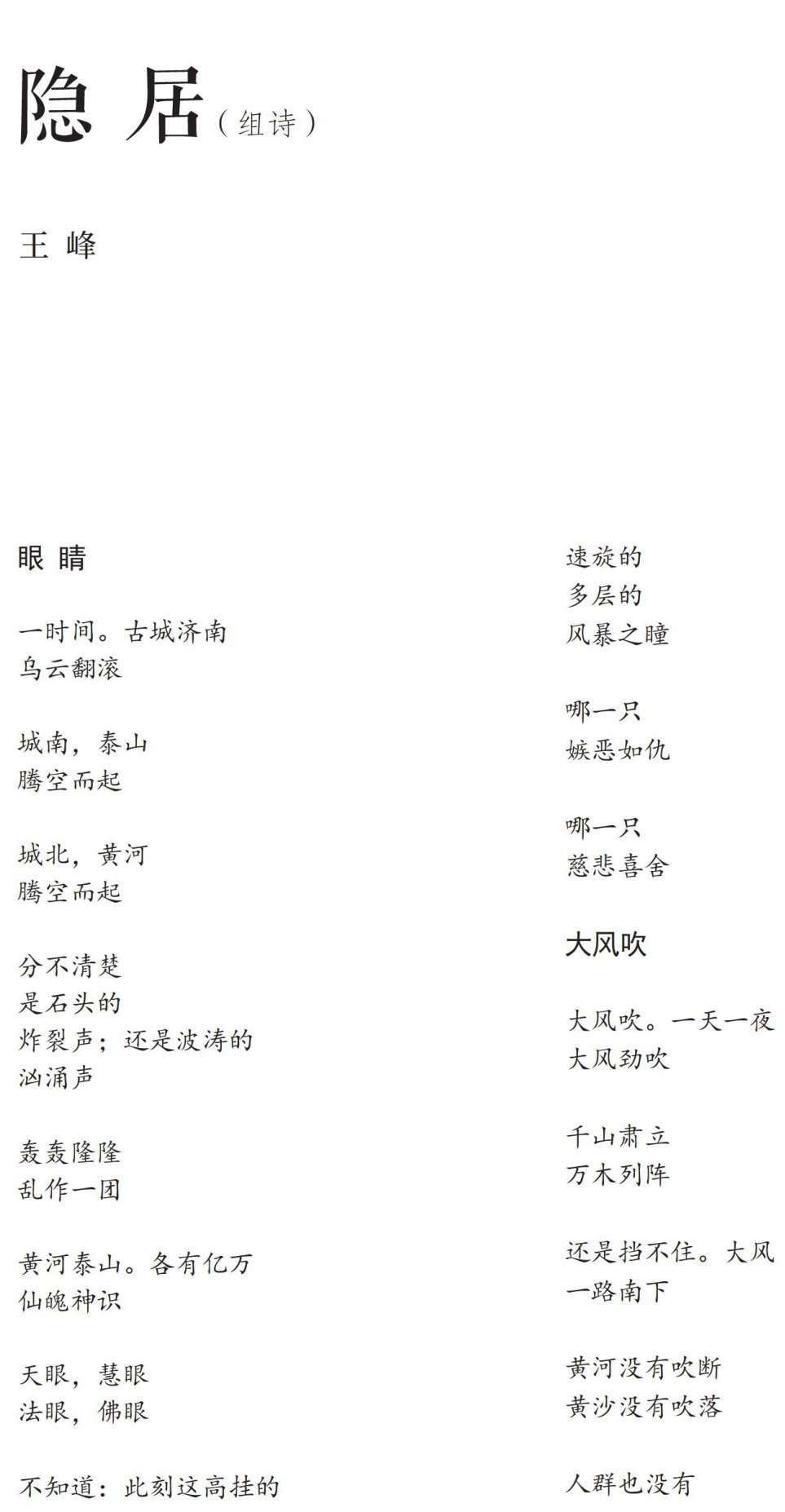
诗歌 | 隐居(组诗)
诗歌 | 隐居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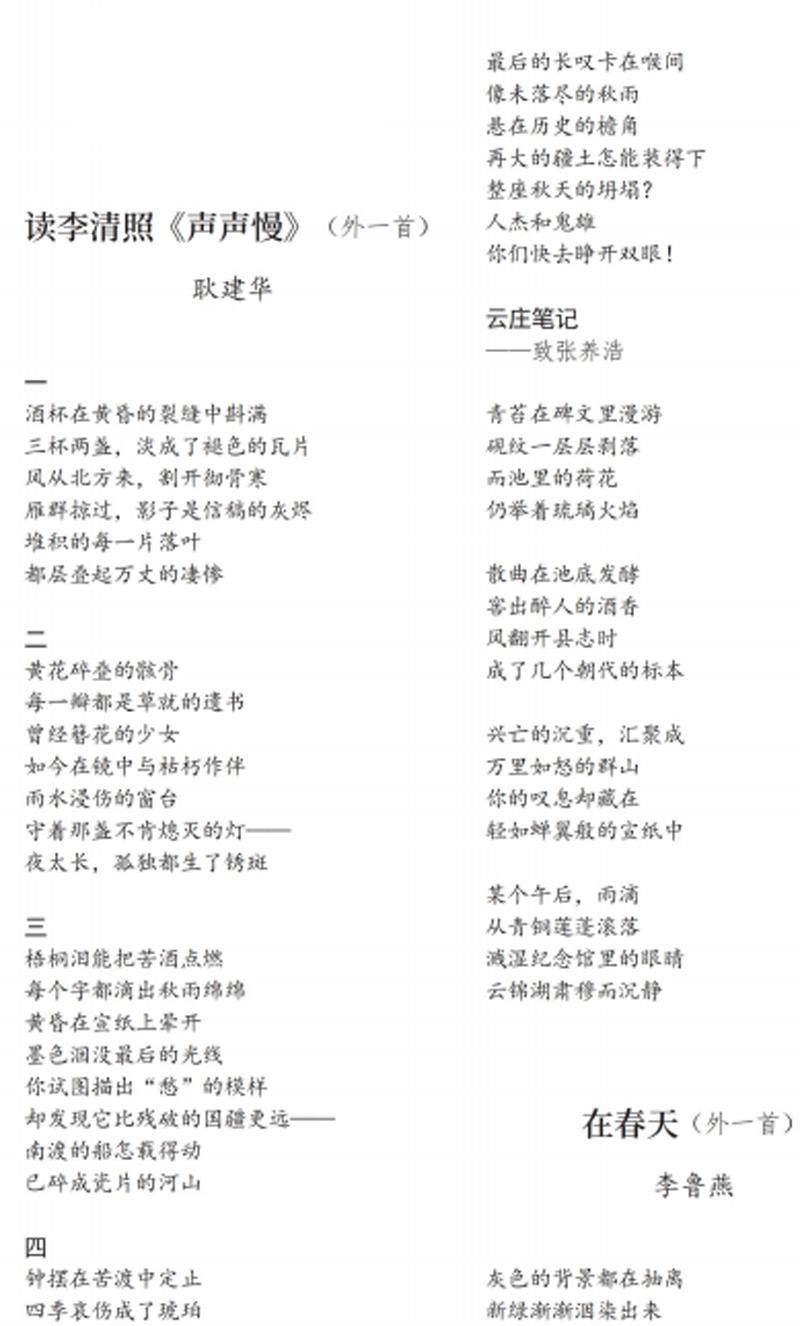
诗歌 | 短诗
诗歌 | 短诗
-
基层作者作品展.东阿阿胶特约栏目 | 只差一头猪
基层作者作品展.东阿阿胶特约栏目 | 只差一头猪
-
基层作者作品展.东阿阿胶特约栏目 | 霍拉山上的女人
基层作者作品展.东阿阿胶特约栏目 | 霍拉山上的女人
-
评论 | 一种“略大于” 的写作
评论 | 一种“略大于” 的写作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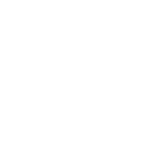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